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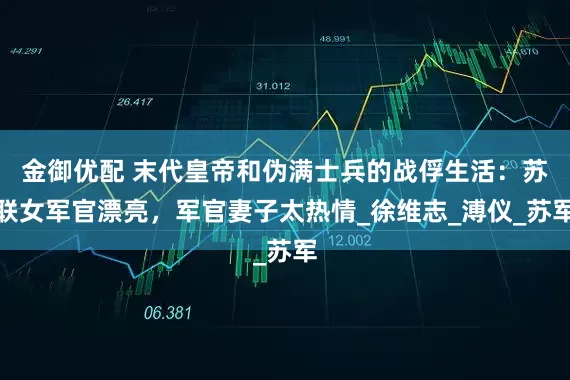
溥仪,作为末代皇帝,于1959年首次获得特赦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从战犯管理所步出自由的。事实上,从1945年到1950年,溥仪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两个地方,直到他最终被转送回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。
当溥仪回到祖国,刚从火车上下来时,他紧张得几乎手脚冰凉,抓起一个苹果,不顾一切地咬了下去。很多人可能以为他在苏联的日子过得极其困苦,无法得到食物,但溥仪在回忆录中坦言:“我看到四个兵士腰间插着盒子枪,我心里想,完了。于是我只是不知味地咬着苹果,艰难地咽下去,心里预感着自己可能会被五花大绑送上刑场。”
溥仪本以为自己会因为被送回国而面临严刑酷刑,直到战犯管理所的首长耐心开导,他才松了口气。回到祖国的溥仪开始回忆自己在苏联赤塔与伯力的五年拘禁生活。顺便提一下,赤塔和伯力原本是中国的土地。赤塔曾是元朝的领土,而在1689年的《尼布楚条约》签署后,成为了俄国的领土;伯力则在1860年随着《中俄北京条约》的签署,正式划归俄国管辖。
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,苏联关押了大量的战犯和战俘,其中不仅包括末代皇帝溥仪,还有许多伪满洲军的士兵。今天我们通过溥仪和普通士兵徐维志的亲身经历,来了解这些战俘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。徐维志是伪满陆军第二十五团二营的重机枪连士兵,类似于《地下交通站》中的黄金标,虽然身份不同,但两者的服装非常相似。
展开剩余78%徐维志的倒霉开始于1945年1月。当时他作为滨江省五常县(今黑龙江省五常市)许窝堡小学的教师,接到征兵通知书,经过体检合格后,于3月1日被征召入伍。经过短暂的训练后,他和队伍一起准备开赴前线与苏军作战。然而,在他们还未到达前线时,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。
虽然日本投降使得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,以为终于可以放下武器回家,但没想到团长竟然秘密召开了军官会议,决定投奔国民党。这一决定引发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们的强烈反对,导致了内讧。当大家正在争论时,苏军突然抵达,团中的1200多名士兵无奈地缴械投降,成为了苏军的战俘。
很多人认为,被苏军俘虏后就只能去西伯利亚挖土豆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虽然战俘营内确实有一些恶劣的待遇,特别是对于德军和日军战俘,但对于中国战俘,苏军的待遇较为宽松。溥仪和徐维志都是幸运的例子。溥仪在赤塔的生活可谓是颇为优渥,他有专人伺候,并且享受着每日三餐丰盛的俄餐以及俄式的午茶。每次午饭与晚饭之间,还有许多娱乐设施和活动来消磨时间。
溥仪甚至幻想过,如果苏联与英美结成更深的同盟,他或许能够转移到英美去度过晚年,并且带着一大批珠宝首饰过上富足的生活。溥仪曾多次向苏方申请留在苏联,但最终还是被送到了伯力。在那里,他虽然不再享有苏联姑娘的贴身照料,但依然过得舒适。他的家人会帮他整理屋子,端饭、叠被,甚至为他洗衣服。
然而,溥仪虽受宠若惊,却也并非完全满足。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,他不但丢弃了部分珠宝,甚至将一些珍贵的首饰烧毁或者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。事实上,苏军在处理战俘时,并不会像对待德军和日军那样严苛,他们不会搜查中国战俘的随身物品,也不会强迫他们从事过于艰难的劳动。徐维志便是一个典型例子,他在回忆录中写到,苏军不搜查战俘的随身物品,也没有严酷的刑讯和劳动要求,甚至让他们为苏军军官家属砍木柴、劈柴,而这类工作也让他十分高兴。
不过,虽然苏军对战俘关怀备至,但徐维志和其他战俘的待遇依然远不及溥仪。他们的饮食一开始较为简陋,主食是高粱米和小米,副食则是饨蕨菜干、窝瓜干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待遇逐渐改善,1946年3月,战俘们开始能够享受牛肉、大白菜、大米等食物。徐维志和其他战俘一度分成小单位自己准备伙食,“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饭,吃饭,夜里楼内外常常是一片火光,吱吱作响。对于我们这些战俘来说,这种改善简直像是过上了御宴。”
当然,不是所有战俘都懂得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改善。有些伪满士兵,尽管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,仍旧怀念当年在伪满洲国当兵时对百姓的压迫。有人甚至会开玩笑地说自己曾经从百姓家中顺走瓜果,或者骑着毛驴拿着军刺捅人的屁股。与此同时,他们还常常谈论与苏军军官家属的互动,尽管有时候这些士兵并没有完全珍惜苏方提供的待遇。比如,某些战俘在享受了苏军军官妻子的好食物后,依然马虎应对工作,心思都在窥视这些女军官的美貌。
徐维志曾在战俘营中经历了一个令他难忘的时刻:某天,他看到两位骑马巡视的年轻苏联女军官,身穿军装、笑容可掬,带着威严但温和的气质。徐维志一时看得呆了,心里完全无法平静下来,这个情景在他心中深深烙下了印象。
最终,徐维志在回忆录中总结道:“当我年老时,再回望二战中其他战俘在德军和日军监营里遭受的酷刑与死亡,苏联对待战俘的人道主义与这些惨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”
溥仪和徐维志确实是幸运的,如果他们身处德军或日军的战俘营,恐怕连写回忆录的机会都没有。
发布于:天津市红腾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